城市里的结婚,新娘子需用小汽车接送。租辆超长的凯拉克或豪华奔驰已是很平常的事情。每当节假日,我们在都邑里时常见到十几辆结婚用的小轿车,浩浩荡荡,鱼贯而行,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国宾车队还威风气派。北京、上海有些新郎、新娘,两家便是前后堂或旁边邻舍,动动腿,几分钟即抵家门。平时情侣来往,三步两步,不请自到,可成婚大喜日,没有小汽车迎送,新娘就不迈出家门。于是请来轿车,在表面兜上一圈儿,风光风光,再进新部家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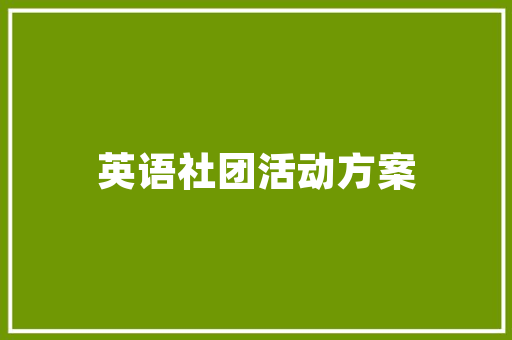
民俗学学者仲富兰有过这样的思考和描述:
他所认识的一对恋人,从小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。终年夜后,各自经历了一番弯曲和坎坷,末了终于喜结良缘。他们家住上海徐家汇附近的同一条弄堂里,按凡人想来,邻上加亲,喜上加喜,婚礼礼节上总可以简化了吧。可是不! 临办喜事前,女方的母亲一定要坚持让女儿坐轿车出嫁。做新郎的小伙子只好要了两辆出租汽车,迎亲那天,载着新娘,从他们家的那条弄堂出发,经徐家汇、淮海路到外滩兜上一圈儿,然后再返回原地。在鞭炮声中,新娘下轿车,然后举行了各种礼节才算完成了这桩好事。
这就让人十分纳闷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近尾声了,为什么姑娘出嫁还要那么讲究呢?最近又听说一对已经成婚一年多的夫妻,由于当初参加集体婚礼,婚事简办了,如今看到别的新娘都坐着轿车到男方家,颇有悔不当初之感。女方便吵着要
补办婚礼。男方无奈,只得再次宴请来宾,雇上出租汽车进行了一次“补坐轿车“的仪礼。
那么,为什么都邑中的青年对坐轿车那么感兴趣呢?细细想来,又觉不敷为怪。小汽车很多人都坐过,但结婚坐轿车,意义不同平凡。个中包含这样的文化生理:追求正统并意在向社会宣,我们的婚姻是明正的,是正宗夫妻而不是私下的苟合。在生活中常听到一些小夫妻拌嘴,女的受了委曲,就会这样对男方嚷着说“你不要弄错了,我不是自己走到你们家来的,你用轿车接我来的。”显然,要坐轿车,包括把婚事办得隆重热烈,追求一定的场面,都和这种文化生理有关。因此,只管经由婚姻登记,婚姻受到法律的保护,然面对于诸如坐轿车之类的习俗,人们依然乐此不疲。
旧时富费人家要用花轿,而穷汉家用不起肩舆的,就用推车迎。肩舆或车内一样平常都要有一个压轿重或压车。若是用肩舆迎的话,肩舆前面走着一个夹红毡的,他专管逢村落过店时放一阵鞭炮。肩舆前面还要有:打旗的六人、打锣的二人、鼓乐一班(唢呐、笙、罄等四至六人)、打灯笼的二人、拿火把的三人、挑鸡的一人(用一对牛笼嘴,里面装一只公鸡、一束艾、两棵并根葱)。到达新外家时,亲家母要配上一只母鸡,把艾、葱留下,挑鸡的把一对鸡子挑回男方家中。肩舆到达女方家中,卖力招待的人出来欢迎他们进屋,向压轿童施礼,恭请下轿。然后女方家设大略的酒菜欢迎他们这些迎客。
坐花轿的意义(二)
沈从文的小说《萧萧》,描述了湘西百姓的结婚风尚: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,到了农历十仲春是整天有的事情。
唢呐后面一顶花轿,两个役夫安全稳稳地抬着,轿中人被铜锁锁在里面,虽穿了平时没上过身的体面的红绿衣裳,也仍旧得号大哭。在这些小女民气中,做新娘子,从母亲自边离开,且准备做他人的妻子,将同一个陌生的男子汉在一个床上睡觉,做着承宗接祖的事情。这些事情想起来,当然有些害怕,以是照例以为要哭哭,就哭了。
汉族民间新娘对外家的依依不舍之离去情,大多以女儿不愿装扮上轿表现出来。女方家不会让迎亲军队轻易进入家门。迎亲军队到女家门外,女方大门紧闭,要难堪男家。于是迎亲的人和新郎上前拍门,口称“吉时已到,请新娘上轿”之类的话。女方家人则隔着门缝,要男方吹鼓手演奏一些曲牌,并向院中扔一些糖果之类食品,然后大门吱嘎嘎地打开,一阵铜钱雨和一小包茶叶骤然飞出,这叫“撒满天星”。在广东屯子,新娘上轿提高行“安凤”礼。
按俗请了一位“正装装扮大马”,一位“代步装扮大马”,卖力替新娘梳凤髻,戴凤冠。但新娘总是不肯服帖服帖地让她们装扮,躲在闺房不肯出门,来表示舍不得离家。闺房中有一帮姐妹护卫着她,他们把房中所有照明的东西都藏起来,待装扮大马”一走进房,灯火立时吹熄,“装扮大马”与姐妹们展开打劫新娘之争,阴郁中你争我夺,你拉我拖十分激烈,但末了的胜利总是属于“装扮大马”的,新娘哭着被拖出闺房。
“安风“完毕,新娘由“装扮大马“和大妗姐扶着拜别先人,对着大门拜天拜地,向父母众亲拜别后才上轿。众姐妹拥着花轿送新娘上路,没走多远,轿又停下了,姐妹们给新娘奉上清茶一杯,进行末了话别,俗称“谢轿”。在民间社会,肩舆的出发有一定的规矩,民众历来极为重视,肩舆(现在则是车辆)的朝向,行进的路线都要按照规矩。肩舆回去的时候所走的路线不能和来的时候重复,而要按逆时针方向行走,即来时走右边,回去时走左边,重复的话就会生男不生女或生女不生男。花轿一出发,就意味着婚礼的正式开始。
用花抬新媳妇的形式五花八门,各具奇趣。
旧俗结婚仅为合二姓之好,以上事宗庙,下以续后世,以是,婚后的生子便成为过门后的一项重大任务,倘若女子婚后不育,则后果将不设想。于是在新娘上轿前,依依不舍的离去之情又表现为父母为求新娘日后幸福,保佑她快生子、多生子。许多地方都以风趣的风尚将这齐心专心境展示于众。
浙江绥云一带准备上轿的新娘,衣服的前襟里准备了许多铜钱,当新娘出轿时小铜钱如天女散花似的撒落地下,一群小孩欢呼笑着又捡又抢,俗称“鲤鱼撤子,形象地表达了新娘进夫家可如鲤鱼般地生子育女的欲望。位于湖北西部的神农架地区,新娘在上轿前要由舅舅把她抱放在量谷的斗上,站在斗梁上面,新娘手持一把筷子,唰的一声撒落在外家堂屋地上,才挥泪上轿。“撒筷子”意寓外家愿望她快快生子。广东饶平一带新娘上轿前须用石榴等12栽种物的花或叶泡水沐浴。浴毕,坐在浴盆中吃下两个煮热的鸡蛋,以祈求女儿多生多育。
浙江武义一带新娘上轿后,由长喇叭和号筒打头阵,演奏之声一声似哭,一声似笑,甚是逗人。两盏长圆形各标有男家大姓和祠堂名的堂灯紧跟后面,灯后两面红旗飘飘扬扬,由大锣大鼓,唢呐等乐器组成的喜乐队演奏着喜乐,两个人各背着
一支连叶带根的“子孙竹”,上面还挂着盏小红灯,尾随乐队,花轿吱悠吱悠地跟在子孙竹后面,别有一种派头风光。
山东一带用花轿抬新妇旧俗还有“小娶”和“大娶”之分。小娶便是抬一顶肩舆去迎亲,去时由压轿的来女家,迎上新娘子回来;大娶则须抬两顶肩舆,新娘乘的一顶叫“花轿”,新郎乘的一顶叫“官轿”,鼓乐喧天,又是另一种派头和风光。
